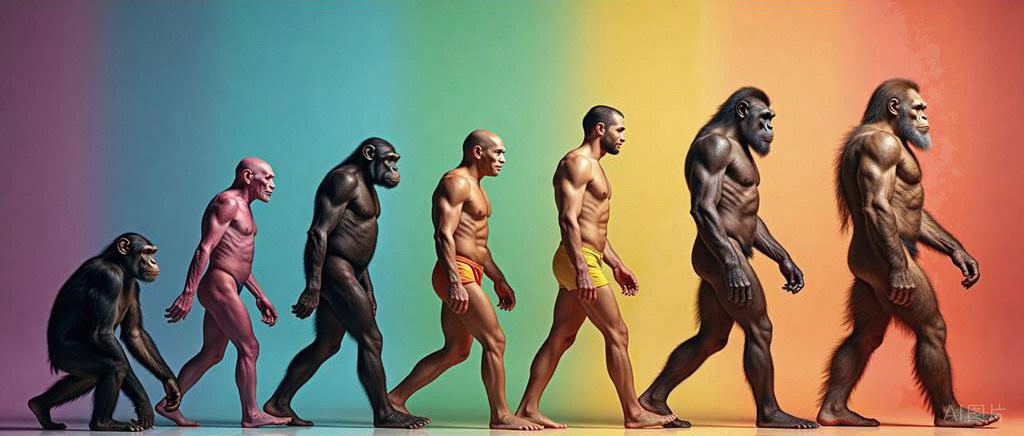本文翻译自Jerry A. Coyne 和 Luana S. Maroja所合著的The Ideological Subversion of Biology一文.
原文网址:https://skepticalinquirer.org/2023/06/the-ideological-subversion-of-biology/
原文发表于科普刊物《Skeptical Inquirer》的网站上,两位作者均为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是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以其在物种形成和遗传分析领域的卓越工作而闻名。除了学术成就外,科因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的著作《为什么进化是真的》(Why Evolution Is True)是一本科普畅销书。露安娜·马罗雅(Luana Maroja)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教授。她出生于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涵盖了多种生物,包括蟋蟀、蝴蝶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物种形成和杂交遗传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除了学术研究,马罗雅还积极撰文捍卫学术自由,并批判意识形态对科学的侵蚀。
简介:生物学正受到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限制研究领域、操控学术语言以及主导教学内容,削弱了科学开放探究的传统。推动这一局面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生物学平均主义思想,它否认遗传对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影响,利用政治手段压制异见,造成研究者的寒蝉效应,并从根本上损害了科学的智识基础和实践价值。本文列举了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生物学领域广泛流传的六种错误观念,并深入探讨了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生物学的颠覆性危害。
原文较长,本站将其分三次发表。本文为这一系列的第三篇,也就是最后一篇。前两篇中两位作者讨论了和生物性别、性别差异、进化心理学、遗传差异,以及种族相关的议题。这一篇里作者讨论了所谓的土著“认知方式”,并对全文做了总结。
本文长度约7千字,阅读时长约23分钟。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进步主义,土著知识。
正文
6. 土著“认识方式”等同于现代科学,应该像现代科学一样受到尊重和教授。
由于新西兰的毛利人和美洲大陆的北美原住民等土著群体曾经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其传统知识体系常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独立于所谓”殖民主义科学”发展起来的认知体系,并被某些人认为具有同等价值。新西兰政府甚至要求在教育体系中给予土著认知体系与现代科学同等的地位,这一政策不仅适用于科学课程,还延伸至中学教育的所有学科领域。与此同时,南非也在推进生物学的去殖民化进程。在著名的《自然》期刊上,一篇文章呼吁南非在药理学领域进行去殖民化,专注于本土草药疗法,以“使课程扎根于本土经验”。虽然这种做法确实为学术研究增添了本土特色,但过度强调地方经验可能会使学生偏离现代药理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认知体系Mātauranga Māori融合了从反复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包括其波利尼西亚祖先的航海技术以及毛利人获取和种植食物的方法),同时也涵盖了神学、民间信仰、意识形态、道德和传说等非科学领域。然而,所有这些内容都被认为与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具有同等的教学价值。例如,毛利学者提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毛利人的祖先)在七世纪率先发现了南极洲。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可能源于对口头传说的误解。事实上,南极洲最早是由俄罗斯人在1820年发现的。尽管如此,新西兰最负盛名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仍然向毛利人提供了66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探索这一虚构的叙事。此外,Mātauranga Māori中的传统草药和精神疗法也得到了复兴,其中包括将吟唱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虽然这些本土疗法有时可能有效,但它们几乎从未经过医学黄金标准——随机对照试验——的验证。
土著民族的认知体系往往包含丰富的实践智慧,这些智慧源于对当地环境的细致观察和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例如,在Mātauranga Māori中,就包含了古老的航海技术和捕捉鳗鱼的最佳方法。然而,这些实践智慧与现代科学对自然界的系统性、客观性研究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科学并不涉及对神灵或灵魂的假设。将土著认知方式与现代科学混为一谈,不仅会使学生对什么是知识感到困惑,还会对科学本身的性质感到困惑。诚然,现代科学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当时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权,且科学界主要由白人主导。这种偏见确实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机会,但这并不能成为将科学——作为产生关于宇宙的公认知识的最佳方法——贬低为”西方”或殖民主义产物的理由。(”西方科学”这一说法本身已完全不合时宜,并且冒犯了许多在其他国家从事同类科学研究的人们。)
一个涉及土著文化与现代科学对立的典型问题是法医人类学领域:即通过研究人类遗骸和人工制品来探索古代社会。以北美为例,当地发现的人类遗骸往往会被美洲原住民认领为祖先遗骨,从而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因为这些遗骸被视为现代土著群体的古代成员。事实上,根据联邦法律规定,这些骨骼和其他人工制品必须归还给提出认领的土著群体。这些遗骸必须在未经科学研究的情况下重新安葬,即使人类骨骼与发现地的美洲原住民之间并无明确的血缘联系。在”基内威克人”(Kennewick Man)的案例中,土著群体提出的”科学”主张包括一位美洲原住民领袖拒绝承认其祖先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而来的观点。这位明索恩先生表示:”根据我们的口述历史,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祖先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而来的。”
圣何塞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体质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韦斯(Elizabeth Weiss)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受害者。她致力于研究来自加利福尼亚、距今500至3000年前的人类骨骼。然而,仅仅因为从事这项研究,韦斯就遭到了大学的降职处分,并被禁止接触所在部门的骨骼收藏。更糟糕的是,她甚至无法研究这些遗骸的X光片,也不能展示存放遗骸的盒子的照片。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伯克利(Berkeley)等许多其他大学,它们正在归还或重新埋葬文物和古代骨骼。其结果是:宝贵的人类历史和人类学资料变得遥不可及,因为这些遗骸和文物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显然,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在进行科学研究和DNA采集之后再进行埋葬。目前的政策阻碍了我们了解自身的历史。
推广这些非科学的认知方式,源于一种试图通过将受压迫群体的文化提升到与科学同等的认知权威地位,来颂扬这些群体的愿望。哲学家莫莉·麦格拉思(Molly McGrath)将这种观点称为”神圣受害者的权威”。在世俗层面,这种权威源自后现代主义观点,即科学仅仅是众多”认知方式”中的一种,而科学的“霸权地位”反映的是权力关系而非学术成就。这种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左右两派某些人的支持,他们常引用”科学从来都是政治性的”这一口号。
像圣经的创世论一样,许多原住民知识体系都蕴含着丰富的灵性或神学元素。这些元素并非源自实证,而是基于权威或启示。若要将这些知识中的任何一部分融入现代科学,首先必须将其中经验性的实质与灵性的虚饰区分开来。正如非宗派牧师迈克·奥斯(Mike Aus)在放弃信仰后对”宗教知识”的描述所言:”并不存在不同的认知方式。只有知与不知,这是世上仅有的两种选择。”
结论
几乎所有由意识形态驱动的生物学扭曲都源于一种激进的平均主义心态。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不同性别、族裔群体以及个体在外表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在行为和心理上几乎完全相同,而大多数行为差异则归因于社会化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化已成为解释以下现象的默认理由:为何数学和物理学领域男性多于女性(而心理学领域女性过多)、为何男性更具攻击性而女性更具同情心、为何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的人在成就上存在差异,以及为何不同群体在科学和整个学术界中的代表性存在差异。尽管社会因素确实会影响这些差异,但人类差异中遗传影响的普遍证据表明,先验地拒绝遗传因素的作用是不明智的。然而,由于流行的“白板主义”意识形态与生物学数据相矛盾,其拥护者不得不通过扭曲生物学事实来使其议程免受数据的影响,从而使其符合他们的信仰。
生物学领域的平均主义以两种方式损害科学。其一表现为威慑效应:这种寒蝉效应抑制了科学家对某些课题的研究与教学。这种影响并非通过直接禁止研究来实现,而是通过向教师和研究人员灌输恐惧,使他们不敢涉足甚至讨论相关话题。仅需几个公开案例就足以震慑众人,例如,那些主张人类仅存在两种性别的人(如哈佛大学的卡罗尔·霍文和南缅因大学的克里斯蒂·汉默)就曾遭到公开羞辱。此外,研究群体差异及其遗传基础的人很容易被贴上性别歧视者、厌女者、种族主义者或优生学家的标签而失去工作。这种手段极为有效,因为哪个力薄儒(liberal)——而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是力薄儒——愿意被贴上这些标签呢?同样,那些拒绝将现代科学与土著认知方式等同视之的人,不仅被视为种族主义者,还被扣上殖民主义的帽子。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研究人员和教授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自我审查,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另一种损害则更为直接:对那些研究偏离生物学平均主义太远的科学家施加要求或进行惩罚。这些惩罚手段包括:取消教授的课程,通过迫害使其陷入困境以致被迫离开学术界;要求他们接受虚假陈述;直接解雇;要求在科学研究中加入非科学元素;拒绝发表那些“不尊重所有人类尊严和权利”的科学论文;扣留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以及将研究资金转移到意识形态驱动的项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曾计划这么做,但很快便放弃了)。
此外,本文未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批评将科学成就作为评判科学或聘用科学家的“过时”标准。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主要来自左派的呼声,主张用更注重群体身份的“整体”方案来取代能力评估。这导致许多大学要求未来的教职员工在工作申请中提交多元化声明(diversity statement),取消了大学申请者提交MCAT、SAT和GRE等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要求,甚至解雇了那些因科学课程难度过高而受到批评的教授。
科学始终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从伽利略因日心说与教会教义相悖而遭受审查开始,这种影响就从未间断。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曾就进化论、疫苗有效性、全球变暖、饮用水加氟等议题展开激烈辩论。然而,当下的情况已大不相同。首先,当前对科学的攻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性,不再局限于单一议题,而是蔓延至各个领域。以生物学为例,争议已不再仅限于进化论这一我们职业生涯中唯一真正的文化论战,而是扩展到了生物性别、群体差异、科学用语规范、生物制品处理,乃至是否存在除现代科学之外认知自然界的有效方法等诸多层面。像格雷戈尔·孟德尔、查尔斯·达尔文和赫胥黎这样的生物学先驱,如今却被简单地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的标签。
如今,对科学的攻击不仅来自公众、宗教信徒或政治权威——这与过去并无二致——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攻击还来自科学家群体内部。一些科学家认为某些研究领域是禁忌,主张限制公共资助数据的公开获取,认为研究资金的分配应基于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价值,甚至要求对那些可能冒犯特定个人或群体的研究论文进行审查或压制。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李森科事件中苏联当局对遗传学和农业科学的扭曲。然而,与那时不同的是,今天是我们自己的同行在试图将科学强行塞入意识形态的单一框架。尽管在当今社会,科学上的非主流观点可能不会像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事关生死,但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研究显然正面临严峻挑战。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推测,过去十年间政治气候的变化,特别是身份政治的迅速崛起,导致了一些左翼科学家——即使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领域来进行意识形态的道德作秀和寻找政治“部落”的归属感。此外,科学界也受到了人文学科中广泛存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当这些因素与许多担心职业损害的研究人员和教师的自我审查结合在一起时,对科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如何才能恢复科学的核心使命——探索自然与宇宙的奥秘?由于意识形态的压力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包括那些掌握科研经费分配和论文评审大权的人,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科学论证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激进的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它排斥事实和理性论证。这也是一种群体忠诚的宣誓。正如史蒂文·平克所解释的,对进化论的抵制并非源于对科学证据的否定,而是作为坚守宗教意识形态的标志,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在原则上排斥进化论。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当前损害生物学发展的准宗教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接受进化论与其说是科学素养的体现,不如说是对进步主义世俗亚文化而非保守宗教亚文化的认同。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其科学素养测试中删除了这样一道题目:”人类是从早期动物物种进化而来的”。这一调整并非如某些科学家所指责的那样,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屈服于神创论者的压力而将进化论从科学经典中剔除。真正的原因是,这道题目与测试中的其他题目(如”电子比原子小”和”抗生素能杀死病毒”)相关性过低,使用它相当于浪费了测试中原本可用于更有诊断价值的题目的空间。换言之,这道题目实际上是在测试宗教信仰,而非科学素养。当题目以”根据进化论”开头,以使科学理解与文化认同相分离时,信教与不信教的考生给出了相同的回答。
因此,如果依据事实无法扭转局势,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显而易见的缓解措施其实早就存在:我们需要一种在道德上独立于生物学差异的平等主义。正如平克在《白板论》一书中所指出的(第340页):“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类群体相等的实证判断;它是一种道德原则,即个人不应因其所属群体的平均属性而受到评判或限制。”
我们应当重申,科学家的职责在于探索真理,而非决定社会如何应用这些真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都具有同等价值或趣味性,也不意味着科学从未被以有害的方式滥用,齐克隆B(一种杀虫剂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用作种族灭绝的工具)和核武器便是明证。然而,鉴于许多基础研究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我们应当避免对整个研究领域进行全盘否定。如果某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曲解或滥用科学研究成果,科学家们理应挺身而出,予以纠正。
然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许需要从哲学层面进行探讨——即强调根据自然去决定哪些行为是好的、道德的或正常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种做法往往会陷入两个广为人知的逻辑谬误。首先是自然主义谬误,其核心观点可以用一句著名的格言概括:”事实即应当”,或者表述为”自然如何,我们就应该如何”。其次是与之相关的诉诸自然谬误,这种观点认为凡是自然的必然就是好的。
这两种谬误会导致相同的错误。首先,如果我们将政治和伦理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之上,那么我们的政治和伦理观念就会随着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变化而改变。例如,科学家观察到雌性倭黑猩猩通过互相摩擦生殖器来建立社会联系,这一发现被用来证明人类同性恋既不冒犯也不违背道德。毕竟,倭黑猩猩的行为是”自然的”。(类似的同性行为在许多物种中都有报道,并被用于同样的论证目的。)但是,如果这种行为在任何非人物种中都没有被观察到呢?或者如果证明对倭黑猩猩的观察是错误的呢?这是否会使同性恋行为变得不道德甚至犯罪?当然不会,因为开明的同性恋观点并非基于与自然的相似性,而是基于道德原则——道德告诉我们,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没有任何不道德之处。
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人类社会中,往往会被视为令人反感或不道德的。这些行为包括杀婴、抢劫和婚外性行为。正如我们中的一位作者所言:“如果同性恋行为因其与自然界的相似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那么儿童杀手、小偷和通奸者的行为也应如此。”然而,我们并非真正从自然界中推导出我们的道德或意识形态。相反,我们只是选择性地借鉴那些与我们已有道德观念相契合的其他物种的行为。(当人们假装从宗教文本如《圣经》中推导道德时,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忽略不良行为,赞扬良好行为。)
【两位作为力薄儒生物学家的作者显然忽视了他们在这两段文字里的自相矛盾,若真如上文所述那么简单,“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没有任何不道德之处”,那么通奸岂不是也就没有任何不道德之处了。】
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生物学误解,都源于将先入为主的观念强加于自然界。这种做法将古老的谬误颠倒为一种新的谬误,我们称之为”反诉诸自然”的谬误。 这种谬误不去假设“自然的事物必然是好的”,而是认为“好的事物必定是自然的”。它要求人们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棱镜来观察自然世界。如果你是性别活动家,就必须看到两种以上的生物性别;如果你是严格的平均主义者,就必须认为所有群体的行为模式完全相同,且他们的认知方式同样有效;如果你是反遗传论者——即认为遗传差异会助长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白板论”支持者——就必须认定基因对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只能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这种偏见违背了科学最重要的准则,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那句名言所说:”第一原则是你不能欺骗你自己——而你恰恰是最容易被你自己欺骗的人。”
然而,最严重的威胁并非针对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而是直指科学本身的核心。科学的根本原则——以及支撑科学的学术自由——在于探索的自由。那些出于政治考量而将某些研究领域完全排除在外,或蓄意歪曲科学真理的人,不仅践踏了这种自由,更使我们失去了从纯粹、不受限制的研究中可能获得的知识进步与实用成果。
我们并不奢望,仅仅通过呼吁人们关注这些要点并强调反诉诸自然的谬误,就能彻底将意识形态从科学中清除出去。事实上,进步主义意识形态正日益强大,并逐步渗透到科学的各个领域。由于它披着”进步”的外衣,加之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力薄儒,我们中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反对这些对我们学术自由的限制。除非时代精神发生根本转变,除非科学家们最终鼓起勇气大声疾呼,反对意识形态对其研究领域产生的毒害影响,否则几十年后的科学将与今天的科学大相径庭。到那时,我们是否还能将其视为真正的科学,恐怕都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