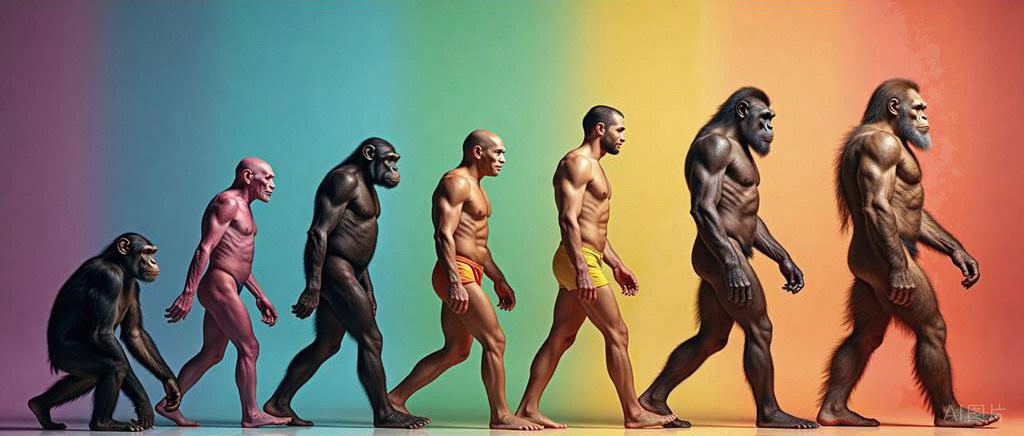本文翻译自Jerry A. Coyne 和 Luana S. Maroja所合著的The Ideological Subversion of Biology一文.
原文网址:https://skepticalinquirer.org/2023/06/the-ideological-subversion-of-biology/
原文发表于科普刊物《Skeptical Inquirer》的网站上,两位作者均为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是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以其在物种形成和遗传分析领域的卓越工作而闻名。除了学术成就外,科因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的著作《为什么进化是真的》(Why Evolution Is True)是一本科普畅销书。露安娜·马罗雅(Luana Maroja)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教授。她出生于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涵盖了多种生物,包括蟋蟀、蝴蝶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物种形成和杂交遗传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除了学术研究,马罗雅还积极撰文捍卫学术自由,并批判意识形态对科学的侵蚀。
简介:生物学正受到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限制研究领域、操控学术语言以及主导教学内容,削弱了科学开放探究的传统。推动这一局面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生物学平均主义思想,它否认遗传对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影响,利用政治手段压制异见,造成研究者的寒蝉效应,并从根本上损害了科学的智识基础和实践价值。本文列举了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生物学领域广泛流传的六种错误观念,并深入探讨了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生物学的颠覆性危害。
原文较长,本站将其分三次发表。本文为这一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中两位作者讨论了生物性别和性别差异,这一篇里讨论了和进化心理学,遗传差异,以及种族相关的议题。
本文长度约7千5百字,阅读时长约25分钟。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进化心理学,遗传差异,种族。
正文
3. 进化心理学,即研究人类行为的进化根源的领域,是一个基于错误假设的虚假领域。
生物学家迈尔斯(P.Z. Myers)加入了对进化心理学(曾被称为社会生物学)持批评态度的人们的行列,他断言:“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前提是错误的。” 即使是那些几乎普遍接受进化论的社会心理学家,对于进化能够解释人类心理、社会态度和偏好的重要方面的观点,也并不十分热衷。
然而,迈尔斯的广为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进化心理学的根本前提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大脑及其运作方式——也就是产生我们行为、偏好和想法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自然选择对我们祖先的影响。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化心理学的反对者却否认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行为。然而,并没有科学依据支持这种二元对立。既然我们的身体能够反映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为什么由同样力量塑造的行为、思想和心理活动,就能免受进化的影响呢? 这种情况只有在人类行为不具备遗传变异性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立,而遗传变异恰恰是进化的必要条件。然而,研究早已表明,我们的行为恰恰是人类最具遗传变异性的特征之一!
因此,由 E.O. 威尔逊的同名著作引发的 70 年代“社会生物学论战”在进化心理学这个新的名称下延续至今,但核心主题依然是人类的例外性——即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受进化力量的影响,尽管进化力量塑造着其他物种的行为。诚然,早期的进化心理学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些“软性”研究,它们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类行为适应性的假设,这些假设既可疑又无法验证。但如今,该领域的解释力已经足够成熟,已经发展到必须认真对待的阶段了。
事实上,据我们所知,进化心理学可以解释多种人类行为。这包括:我们为什么偏爱亲属而不是非亲属——以及更亲近的亲属而非较远的亲属;为什么我们虐待继子女的频率高于亲生子女;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男性和女性在滥交和性偏好方面的差异;为什么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的性嫉妒;为什么某些面部表情能够传达情感;为什么我们害怕蛇和蜘蛛,并对体液感到厌恶;以及为什么我们渴望糖和脂肪。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行为,例如倾向于食用不再健康的食物,源于那些对我们祖先有用的特征,但这些特征现在已经变得无用,甚至有害。
对进化心理学的意识形态污名化,通过隔离这个涉及人性的庞大研究和教学领域,阻碍了我们理解自身这个物种。正如两位进化心理学家所指出的,“据我们所知,美国没有任何一所授予学位的机构,要求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修读哪怕一门进化生物学课程——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教育缺失,它使得心理学与生命科学的其他领域脱节。” 缺乏这些知识,我们就只能将“社会建构”和“社会期望”视为人类行为的唯一来源,而这根本无法解释我们观察到的数据。毋庸置疑,在处理任何涉及人类行为的问题时,我们最好能尽可能全面地解释,即同时涵盖社会和生物学两方面的因素。
对进化心理学的否定,源于一种“白板主义”的人性观,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具有近乎无限的可塑性,行为几乎不受遗传因素的限制。我们之前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使其在左派思想中盛行。史蒂文·平克的《白板论:现代思想对人性的否定》(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书则列举了更多原因,包括:对生物决定论的厌恶;认为后天习得的能力(如语言)不可能同时包含演化而来的能力;错误地将生物因素等同于命运,认为遗传的东西无法改变;以及断然否认生物学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研究个体或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尤其被视为禁忌,因为人们认为这类研究会助长偏见,甚至引发优生学。
4. 我们应该避免研究个体之间行为上的遗传差异。
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秉持白板论的人,常常默认地认为,不应该研究人们在教育成就、智商以及类似特质上的遗传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有来自多种研究途径(如双胞胎研究)的有力证据支持,人们仍然会否认遗传差异的存在。他们认为,这类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人群进行等级排序,助长偏见,并将个体不公平地分流到不同的教育轨道上。然而,事实是,即便在单一族群内部(例如,欧洲裔美国人),几乎每个性状,无论是身体特征还是行为特征,都存在显著的遗传成分。这适用于身高、血压、吸烟或饮酒的倾向、神经质,以及认知能力和教育程度等性状。就后两者而言,个体之间超过一半的差异都源于其基因的不同。但必须明确的是,这些衡量指标反映的是群体内部的差异,而非群体或族裔之间差异的根源。
自从科学发展出对个体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技术以来,相关研究的实用性大大提升。有了这些信息,并对大量个体进行测序,研究者可以将每个可变的DNA位点(即单个核苷酸碱基)与个体的各种特征关联起来,从而确定DNA的哪些部分与特定特征的变异相关。例如,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GWAS) 已经发现了近 4千个与教育程度相关的基因组区域。令人着迷的是,这些基因中有许多主要在大脑中活跃。借助 GWAS 研究,现在仅需分析个体的DNA,并根据其所在人群的大量样本计算出其个体的“多基因评分”,就能对一个人的外貌、行为、学业成就和健康状况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甚至可以在胎儿的 DNA 上进行这种预测。
GWAS分析为有益的干预措施提供了诸多可能性,尤其是在监测个体可能罹患的健康状况方面。然而,GWAS评分在教育成就方面的应用价值更具争议性。诚然,遗传差异在我们所认为的“智力”的诸多方面发挥作用,但目前通过社会和教育改革,而非使用多基因评分,更容易实现平均化的发展前景。
然而,了解教育成果背后的遗传变异,未来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如果我们发现某些遗传变异使得个体对教育或社会干预措施格外敏感,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及早对这些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此外,这些遗传研究也有助于识别环境因素的影响:如果两个拥有相同多基因评分的人最终生活境遇大相径庭,那么他们的环境究竟有何不同?尽管存在争议,但进行此类研究仍然具有其价值,原因便在于此。
大多数人不会反对了解自己罹患疾病的遗传倾向,但这种接受度并不适用于行为和认知方面的研究。人们对后者的抵制源于对人性的白板主义认识,这种观点否定任何遗传决定因素,并认为我们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遗传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有人宣称,对身体特征和疾病以外的任何事物进行遗传研究,都与过去的优生学和类似的歧视行为有关联。
事实上,人们对行为遗传学研究的恐惧和回避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甚至将种族仅仅定义为一种社会建构,并限制研究人员访问那些包含匿名个体遗传构成、健康状况、教育背景、职业和收入信息的公共数据库——尽管这些数据库是由纳税人资助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限制甚至适用于那些并不涉及种族差异的研究。因此,这似乎表明美国政府正试图压制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与学术成就和社会成功相关的行为研究。
5. “种族和民族是社会建构,没有科学或生物学意义。”
这是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避而不谈的问题:有人声称研究种族、民族或种群之间的差异没有任何实证价值。这导致种族相关的研究在生物学领域被视为最大的禁忌,它们被认为本质上是种族主义且有害的。然而,上文引述自《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编辑的断言,其实是错误的。
在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之前,我们想先强调,我们更倾向于使用“族裔”甚至“地理种群”这两个词,而不是“种族”。“种族”一词因其与种族主义的历史关联,已经变得过于政治化。此外,诸如白人、黑人和亚洲人等旧有的种族名称,都与过去常见的错误观念相关联,即认为种族可以轻易地通过少数几个特征来区分,它们在地理上相互隔离,且具有显著的遗传差异。事实上,今天的人类物种是由地理上连续的群体构成的,这些群体在遗传变异的频率上只有小到中等的差异,而且群体内部还存在更小的群体,这意味着可能存在无数个“种族”。尽管如此,人类种群确实表现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遗传差异。这些微小的差异,累积在数千个基因上,便导致了种群之间显著且常常具有诊断意义的差别。
即使是旧的、过时的种族概念,也并非完全没有生物学意义。一组研究人员对超过 3600 名自认为是非裔美国人、白人、东亚人或西班牙裔的人进行了广泛的基因样本比较。DNA 分析显示,这些人群分别属于不同的遗传簇,而且个体所属的遗传簇与其自我认定的种族分类的匹配率高达 99.84%。这有力地表明,即使是旧有的种族概念也并非“没有生物学意义”。考虑到过去人类流动性受限,各人群主要在地理上彼此隔离地进化,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较为特殊的是其中的“西班牙裔”,它是一个相对较晚近才形成的混合人群,而且从未被视为一个种族。正如任何进化生物学家所知,地理隔离的人群随着时间推移会在遗传上产生差异,这正是我们能够通过基因来相当准确地推断人群来源的原因。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我们轻松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的能力,证实了自我认定的种族与遗传分组之间的高度一致性。一项针对 23 个族裔群体的研究发现,他们可以被划分为 7 个大的“种族/民族”群体,且每个群体都与世界上的不同区域相关联。更精细的分析显示,对欧洲人进行的遗传分析表明,他们的遗传构成图与欧洲地图的匹配度之高令人惊讶。事实上,大多数欧洲人的 DNA 甚至能将其出生地精确到方圆约 800 公里以内。
这些民族集群有什么用处? 让我们从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说起:通过基因推断个人血统的能力。如果不同族群之间没有差异,这项任务就无法完成,像 23andMe 这样的“血统公司”也不会存在。但你甚至不需要分析 DNA 序列就能相当准确地预测族裔。 身体特征有时也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人工智能程序仅通过胸部 X 光扫描,就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受试者自我报告的种族。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对全球各地人类种群的遗传分析不仅帮助我们追溯了人类多次从非洲向外扩张的历史轨迹,还能准确测定智人(Homo sapiens)在不同地区殖民的具体时间。近年来,随着”化石DNA”测序技术的突破,这一研究变得更加便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获得了来自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和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等古人类群体的化石DNA,这些古代数据与现代人类基因组的对比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些现已灭绝的群体曾与现代智人的祖先发生过基因交流,并至少产生了部分可育后代——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现代人的基因组中都保留着少量尼安德特人的DNA。尽管考古学和碳14测年法在重建人类历史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如今它们已被对现代人和古人类DNA的测序技术所超越。
此外,对种群进行遗传学研究具有医学意义。许多遗传性疾病与特定族裔存在关联(尽管并非绝对),例如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可导致婴儿期发育退化和死亡)、镰状细胞性贫血、囊性纤维化以及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等。这些关联性使得诊断和产前咨询更加精准高效,因为可以根据族裔背景重点关注潜在的医疗问题。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病率在不同族裔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疾病往往同时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治疗时需要综合考虑饮食和生活方式。对个体和群体进行遗传分析仍可为这些复杂疾病的治疗提供重要参考。基于特定族裔的GWAS分析可以通过检测婴儿甚至胎儿来评估各类疾病的风险。如果提前了解自身的患病风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进行预防性干预,将有助于降低老年时期罹患重大疾病的可能性。
幸运的是,针对不同族裔群体的 GWAS 数据已开始被收集。医学界已认识到,开展对不同族裔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疾病机制和缩小健康差距具有关键意义。这是因为某一族裔群体的遗传研究结果往往无法直接推广到其他群体。例如,近期一项关于痴呆症的 GWAS 研究发现,某些基因组区域会增加美国黑人罹患痴呆症的风险,但对美国白人群体则无显著影响。这一发现表明,预测未来痴呆症风险的基因在不同族裔群体间存在差异,相应的干预措施和治疗方法也可能需要因族裔而异。
最后,将遗传学与族裔联系起来在证据学领域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这些应用包括通过血液、组织或精液样本预测犯罪者或受害者的外貌特征(如面部特征、眼睛颜色、皮肤和头发颜色),或者利用古代DNA推测古人类可能的外貌。例如,我们现在了解到,一些尼安德特人拥有白皙的皮肤和红色的头发,而深色皮肤和蓝色眼睛可能在几千年前的欧洲智人中相当普遍。
然而,在文化论战围绕遗传学的核心争议中,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特征差异成为焦点,其中智力差异更是被视为最敏感的禁忌话题。鉴于这一研究领域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任何研究人员都应谨慎行事,因为几乎任何研究结果——除非证明所有族群在全球范围内完全一致——都可能被用来为偏见和歧视提供依据。事实上,仅仅是撰写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章,就导致许多科学家遭受严厉制裁,他们”发现自己被谴责、诽谤、抗议、投诉、拳打、脚踢、跟踪、吐口水、审查、解雇,乃至被剥夺荣誉头衔”。一个典型案例是俄亥俄州非终身教职教授博·温加德(Bo Winegard),他仅仅因为暗示种族群体间可能存在认知差异就被解雇。正因如此,大多数生物学家都选择远离这一敏感话题。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智商和人生成就的显著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早已为人所知,且可以通过标准化测试轻易测得。关键在于探究这些差异的根源:是源于遗传差异、社会问题(如贫困)、历史与当下的种族主义、文化差异、教育机会的匮乏、基因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还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收养研究、混合民族群体的分析以及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目前,基因组分析主要聚焦于教育成就——这一指标与智商评估和人生成就高度相关——但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欧洲白人后裔。当将这些欧洲白人的GWAS评分应用于其他群体时,其预测效力几乎丧失殆尽。这种预测能力的下降涉及群体间的遗传差异,包括影响教育成就的基因子集的不同、相同基因在不同群体中的变异形式,以及基因及其变异与环境相互作用方式的差异。结论是,将一个民族群体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于另一个民族群体并非易事,每个群体都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
还有两个问题使得分析群体间行为和认知差异变得困难。首先,这些性状通常受到遍布整个基因组的数百甚至数千个基因变异的影响。其次,这些基因在染色体上与其他基因相互连锁。总而言之,这意味着许多决定外貌的基因(如肤色、面部结构、头发质地)——也就是那些提供关于某人种族信息的基因——与包括影响教育程度的基因在内的其他基因连锁在一起。由于染色体上彼此靠近的基因往往会一起遗传,我们无法完全区分影响外貌的基因和影响教育程度的基因。如果群体间成就的差异至少部分源于社会因人们外貌不同而给予的差别待遇(例如,通过偏见和种族主义),那么“外貌基因”所引发的社会影响就会与“学术成就基因”的直接影响混淆,难以区分。
尽管很难完全区分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但理解不同群体中的遗传效应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以GWAS研究为例,针对不同族裔群体分别开展的研究能够揭示与教育成果相关的基因变异是否存在群体间差异,或对环境干预的反应是否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假设某种基因变异与甲状腺功能相关;进一步设想,那些降低甲状腺功能、导致碘缺乏的基因变异与较低的教育成就相关,而高表达的变异则无此关联,且这种低碘变异在白人群体中比在亚洲群体中更为常见。(这一假设并非空想:研究表明,碘缺乏可使智商降低多达15分,而基因可能影响个体对低碘饮食的反应。)基于这一发现,一个简单的干预措施可能是:对携带”低表达”DNA变异的白人群体进行碘补充,而对携带”高表达”变异的群体则不进行补充(因为过量摄入碘是有毒的)。这个例子并非牵强附会,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群体中存在许多独特的基因形式(即”私有等位基因”),这些基因可能对行为特征以及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独特相互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研究不同族裔群体间遗传差异的初衷,是为了提升已知DNA个体的人生成就,而非对不同群体的特定特征进行优劣排序。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深入理解群体间遗传差异的本质。当你认识到,尽管我们聚焦于与成就相关的特定族群的DNA片段,但最终目的是帮助每个人发挥最大潜能时,许多针对此类研究的质疑便会烟消云散。
因此,我们认为,不应将针对群体内部及群体间认知或教育水平的研究妖魔化、禁止或自动拒绝发表,相关数据也应公开透明。毋庸置疑,科学家们应对此类研究保持审慎态度,警惕其被滥用或曲解。然而,归根结底,我们很难否认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越深入——包括遗传学领域——就越能在社会政策制定中取得更大成就。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表明,压制智商研究或将此类研究等同于种族主义,其弊端将远大于益处。毕竟,政治平等应是一种道德必然,而非经验假设,而且一个人的价值事实上并不取决于也不应该取决于其智商或受教育年限。
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说得很好:
“人与人之间既存在差异又相互平等,这一概念颇为复杂,需要一种许多人似乎难以企及的道德高度。他们宁愿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将平等与完全相同等同起来。他们又或声称,人类在有机世界中是独特的,只有形态特征受基因控制,而所有其他思想或性格特征都是由‘条件反射’或其他非遗传因素决定的。……基于如此明显错误的假设的意识形态只会导致灾难。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平等的拥护是建立在主张同一性的基础上的。一旦证明后者并不存在,对平等的支持也将随之瓦解。“(Mayr 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