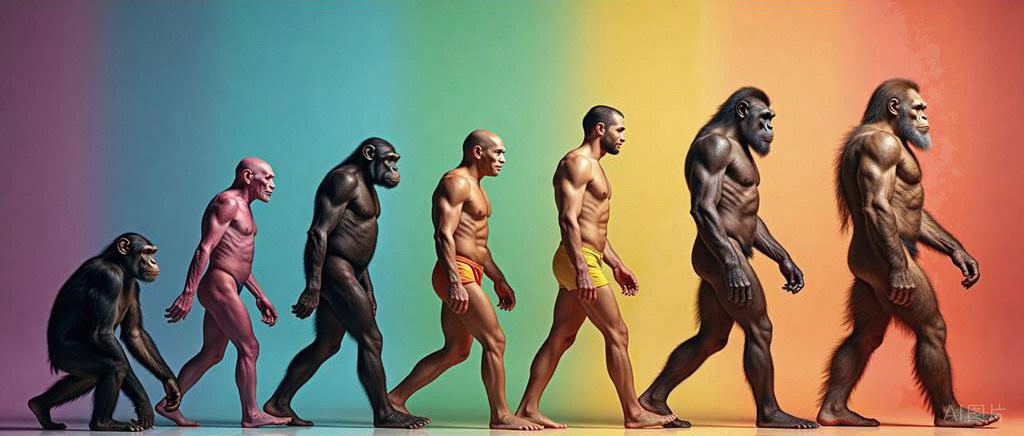本文翻译自Jerry A. Coyne 和 Luana S. Maroja所合著的The Ideological Subversion of Biology一文.
原文网址:https://skepticalinquirer.org/2023/06/the-ideological-subversion-of-biology/
原文发表于科普刊物《Skeptical Inquirer》的网站上,两位作者均为进化生物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是芝加哥大学的荣休教授,以其在物种形成和遗传分析领域的卓越工作而闻名。除了学术成就外,科因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的著作《为什么进化是真的》(Why Evolution Is True)是一本科普畅销书。露安娜·马罗雅(Luana Maroja)是威廉姆斯学院的教授。她出生于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研究涵盖了多种生物,包括蟋蟀、蝴蝶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物种形成和杂交遗传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除了学术研究,马罗雅还积极撰文捍卫学术自由,并批判意识形态对科学的侵蚀。
简介:生物学正受到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威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限制研究领域、操控学术语言以及主导教学内容,削弱了科学开放探究的传统。推动这一局面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生物学平均主义思想,它否认遗传对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影响,利用政治手段压制异见,造成研究者的寒蝉效应,并从根本上损害了科学的智识基础和实践价值。本文列举了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生物学领域广泛流传的六种错误观念,并深入探讨了进步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对生物学的颠覆性危害。
原文较长,本站将其分3次发表。本文为这一系列的第一篇。本文长度约6千字,阅读时长约20分钟。
关键词:政治意识形态,进化生物学,生理性别,基因差异。
摘要:生物学正面临来自进步主义政治的严重威胁。这些政治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划定生物学中不可触碰的禁区,导致相关领域无法获得政府资助,研究成果也难以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它们还规定了生物学家在写作中必须避开的词汇,以及如何向学生教授生物学,甚至干预如何通过技术和大众媒体向其他科学家和公众传播生物学知识。我们撰写本文并非是要断言生物学已死,而是要揭示意识形态正在如何侵蚀和毒害这门学科。从DNA结构的发现到绿色革命的推动,再到新冠疫苗的设计,科学为人类带来了无数进步和深刻的理解。然而,如今我们的开放研究和自由交流的科学的核心传统正受到政治教条的压制。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我们讨论的诸多问题发生在学术界,而许多科学家又因畏惧而不敢发声,公众对这些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可悲的是,当这些问题最终广为人知时,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我们都熟悉进步主义左派与中间派和右派之间的文化论战。过去,这些冲突主要围绕政治和社会文化议题展开,在学术界也多集中于人文学科。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生物学论战”(Sociobiology Wars)和旷日持久的与神创论的斗争之外,我们生物学家一直认为自己的领域可以置身事外。毕竟,科学真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攻击或扭曲具有免疫力,而且我们大多数人忙于实验室工作,无暇顾及党派之争。
然而,我们错了。学术界内外的科学家率先对各自领域展开政治性的清洗行动,他们通过歪曲甚至谎报不便公开的事实来达到目的。他们发起运动,清除科学术语中被认为具有冒犯性的词汇,确保研究稿件中删除任何可能“伤害”被视为受压迫者的结果,并将科研资金转向社会改革。美国政府甚至拒绝公开由纳税人资助收集的遗传数据,如果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能被认为是带有“污名化”倾向的话。换句话说,科学——这里指的是所有科技理工领域——已经受到政治的严重侵蚀,所谓的“进步主义的社会正义”正在排挤我们真正的任务:探寻真理。
在生物学领域,这些变化堪称一场灾难。意识形态分子通过以下手段,已经彻底扼杀了某些研究方向:他们削弱了我们研究那些我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事物的能力,扣留研究经费,控制稿件的政治基调,甚至妖魔化研究领域和研究人员本身。这无疑将损害人类福祉。正如所有科学家都明白的那样——耐热细菌与PCR检测之间的关联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永远无法预知纯粹出于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会带来怎样的益处。而且,培养好奇心本身就具有价值。毕竟,研究黑洞或宇宙大爆炸并不能直接让我们更健康或更富有,但了解这些无疑会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学术自由的侵蚀,无论在智力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对我们造成了损害。
虽然生物学在其他时期和地区,例如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神创论和反疫苗运动中,也曾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但目前的情况更为严峻,因为它波及了所有的科学领域。更令人遗憾的是,科学家们自己——在大学管理层的推波助澜下——也参与了对自身言论的管制。
在这里,我们列举六个案例,阐述进化生物学和有机体生物学这两个我们所处的领域,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或扭曲。在每个案例中,我们首先展示意识形态鼓吹者散布的错误论断,然后简要解释这些论断为何不成立。最后,我们会指出每个错误论断背后的意识形态,并评估其对科学研究、教学和科学普及造成的损害。我们最关注的是生物学研究,即新事实的发现,但研究并非独立于社会影响之外;它与教学以及公众对生物学事实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如果某些研究领域被媒体污名化,公众的理解就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人们对这些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失去兴趣。通过切断或阻碍对生物学的兴趣,媒体的歪曲或污名化最终会剥夺我们理解世界的机会。
我们专注于自身所处的进化生物学领域,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领域最需要捍卫。但我们也要补充说明,相关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其他科学领域也很常见,如化学、物理、数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然而,在这些领域,冲突较少表现为对科学事实的否认,更多地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净化”语言、贬低传统的衡量标准、改变科学领域的人口结构、彻底改变科学的教学方式以及对科学的“去殖民化”。进化生物学尤其容易遭受对科学真理的攻击,因为它触及了最具争议的话题:智人的起源和本质。我们首先从一个关于我们物种的常见误解谈起。
1. 人类的生物性别并非明确的男性和女性二元对立分布,而是一个连续的谱系。
这种说法是生物学中最常见的政治性曲解之一,它是错误的,因为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别之一。你的生物性别,仅取决于你的身体是产生大型、不可移动的配子(卵子,女性的特征),还是非常小且可移动的配子(精子,男性的特征)。即使在植物中,我们也观察到同样的二分法:花粉产生微小的精子,而胚珠则携带大的卵子。大小的差异可能非常显著:例如,一个人类卵子的体积是一个精子的千万倍。而且,每种配子都与产生它的复杂生殖器官紧密相连。正是这两种生殖系统的携带者,被生物学家定义为“性别”。
由于动物和维管植物中不存在其他类型的配子,且我们没有观察到中间类型的配子,因此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性别。尽管许多动物和开花植物是雌雄同体,但这仅仅是将雄性和雌性的功能(以及配子)结合在同一个个体中,并不构成“第三性别”。此外,发育过程中的错误有时会导致双性人(intersex),包括真两性畸形(hermaphrodites)。这种发育变异非常罕见,发生率约为5600分之一(0.018%),同样不代表“其他性别”。(据我们所知,真正的人类真两性畸形案例只有两例,其中一例只能作为男性生育,另一例只能作为女性生育。)
只有在原生生物、真菌和藻类中,我们才能发现存在两个以上不同交配类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配子大小相同(同配,isogamous),它们可以与任何其他交配类型的成员交配,但不能与自身交配。 如果我们放宽对“性别”的定义,这些交配类型可以被视为多种性别,但为了避免混淆,生物学家通常称它们为“交配型”。
因此,从所有实际角度来看,性别都是二元的,这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所有动物和植物。 这种二元性源于自然选择偏好二元性进化。 著名的进化论者罗纳德·费舍尔 (Ronald Fisher) 在 1958 年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任何对有性生殖感兴趣的但又注重实用性的生物学家,都不会将研究重点放在三种或更多性别对生物体带来的详细影响上;然而,如果他想了解为什么性别实际上总是只有两种,他又该如何怎么办呢?”
尽管为了获得有性繁殖的既定优势,并非绝对需要两种不同的配子类型,但二元性别的进化已经多次发生。生物观察和数学模型(我们可以忽略其复杂的细节)都揭示了为什么“二”这个数字如此普遍。从一个具有相同大小配子的祖先物种(“同配生殖”,isogamy)开始,自然选择通常会促进种群分裂为两组具有截然不同配子的个体(“异配生殖”,anisogamy)——要么是小的、可移动的,要么是大的、不动的。二元性别由此进化而来,此后物种会抵御拥有其他类型配子,即其他新性别的个体的入侵。
两性性状的稳定性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不同物种中触发雄性与雌性发育的因素差异巨大。性别分化可以基于不同的染色体及其基因(例如,人类的XX与XY,鸟类的ZW与ZZ,拥有相同染色体的个体在哺乳动物中为雌性,在鸟类中则为雄性);不同的孵化温度(如鳄鱼和海龟);是否拥有一整套或半套染色体(如蜜蜂);是否接触到雌性个体(如海洋蠕虫);以及许多其他社会、遗传和环境因素。自然选择独立地演化出了多种产生性别的方式,但最终都指向两个结果:雄性和雌性。因此,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进化而来且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而非一种人为定义的性别连续谱。
然而,尽管事实如此,二元性别——尤其是在人类中——近来却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冲击。即使在表面上客观地探讨生物性别(sex)和心理性别(gender)时,也有人采纳了一种说法,称人生来就被“指定”了生物性别(例如,“AFAB”即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仿佛这是医生随意做出的决定——一种“社会建构”——而非对生物学现实的观察。就连本应完全清楚情况的进化研究学会(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volution)也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公开宣称生物性别应该被视为一个连续谱。仅仅因为主张人类生物性别是二元的,教师就会被逐出课堂,丢掉工作。正如我们之后将要看到的,这场争议源于对生物学现实(生物性别)与社会建构(心理性别)的刻意混淆。
否认二元性别使我们难以理解生物学中最引人入胜的普遍现象之一:雄性与雌性在行为和外貌上的差异。在鹿、鸟、鱼和海豹等物种中,雄性所展现出的颜色、装饰、更大的体型以及武器,都与雌性在这些特征上的缺乏形成鲜明对比,这是性选择的结果。达尔文最早揭示了性选择这一过程,即雄性之间相互竞争以获得雌性的青睐。这种竞争包括雄性之间的直接对抗,例如鹿的角斗,也包括雄性通过其颜色、装饰和行为来吸引雌性的偏好。自然界中这种近乎普遍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雌性在繁殖上的投入通常比雄性更多,这首先体现在它们产生的卵子更大且代谢成本更高。
最终,这使得抚养子女的重担主要落在雌性身上。由于受制于后代的生育和养育,即使两性比例为1:1,雌性也因此成为更稀缺的可供交配的性别。性选择也解释了行为上的差异:为什么在大多数物种中——包括我们人类——雄性往往比雌性更滥交,而雌性在选择伴侣时则更为挑剔。对于雄性而言,受精只需消耗一小勺精液;而对于雌性来说,卵子数量稀少且“昂贵”,还要经历漫长的妊娠期,以及随后对后代——人类的后代更要花费多年——细心的照料和养育。鹿角、羽毛、孔雀的尾屏、雄性精心设计的求偶舞蹈、以及鸟鸣:这些特征以及其他诸多性状,只有在配子大小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才能被理解为进化的结果。
许多人反对二元性别观,原因在于将生物性别与心理性别——即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性别角色——混为一谈,这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利益。与生物性别不同,心理性别更倾向于呈现连续谱的分布(有在线列表列出了数十种心理性别)。尽管如此,心理性别的分布仍然呈现出驼峰状的双峰模式:大多数人符合传统的男性或女性性别角色,但中间状态的人数也比生物性别中常见的要多。
人们为何要歪曲真相?我们认为,一部分心理性别与两种生物性别之一不符的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希望重新定义生物性别,使其像心理性别一样也成为一个连续谱。尽管这种抛弃二元性别的想法可能出于好意,但它严重歪曲了科学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进化后果。
【译者注:其实所谓的心理性别是一个连续谱的说法也是政治运动征服心理学界的后果。那些声称的几十甚至上百种的所谓心理性别同样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可言。既然人在生理上只有男性和女性,心理上也就只可能有男性和女性,不可能人的心理上会出现一种生理上不存在的性别。有的人因为心理疾病而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困惑,那只是一种病理状态,并不是什么“心理性别”。】
2. 人类男性和女性的所有行为和心理差异都是由社会化造成的。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进化论和遗传学与男女之间的行为和心理差异无关。这便是广为人知的“白板主义”(blank slate,或译为白板论)意识形态,它主张所有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出生时都具有相似的行为倾向。它宣称我们观察到的群体间任何行为或心理差异,都纯粹是包括经济或环境因素影响在内的社会化的结果。
对于生物学家而言,这种部分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无限可塑性的信念的“白板论”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大量研究明确显示,男性和女性在诸多受生物因素影响的行为上存在平均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性偏好、育儿行为、攻击性、滥交倾向、冒险行为、对人与物的兴趣、同理心、恐惧感、空间能力、暴力倾向以及与社会交往相关的特质等等。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平均值:男性和女性行为的分布存在大量重叠,因此个体可能表现出在另一性别中更为常见的特征。例如,有些女性可能比一般男性更具攻击性。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社会化很可能——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导致了男性和女性之间许多行为的差异。
但是,我们能否断言这些平均值的差异完全是由社会化造成的?不能。上述行为的平均差异很可能不仅具有生物学基础,而且具有进化和遗传基础。也就是说,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自然选择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某些行为演化出差异。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通过使用多种评价方法得以确定:评估进化适应性解释的普遍可能性;在其他物种(尤其是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中寻找行为相似性;确定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否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包括狩猎采集者;测试该行为是否受睾丸激素等生殖激素的影响;以及查看该行为是否在预期发育的时间出现。例如,冒险行为和男性之间的攻击性行为在青年时期(即繁殖高峰期)最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如果这些行为是为了帮助男性获得配偶而进化而来。
然而,对许多人而言,即使是提出行为性别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也是一种禁忌,甚至会被视为厌女症的表现。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切尔西·科纳博伊(Chelsea Conaboy)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她声称“母性本能是男性创造的神话”。她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对孩子的关注和行为上存在的明显差异完全是由社会化造成的。但生物学的回答显而易见:虽然确实有一些人类社会将照料子女的重担强加给女性,但母亲比父亲更关注自己的孩子,这种关注是由激素、哺乳、婴儿的啼哭以及看到婴儿等因素触发的——这不仅在所有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包括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在内的数千种其他动物中也同样存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其他物种里并不存在那些白板论者用来解释性别差异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厌女症和父权制恰好在人类社会中创造出与我们在进化上的近亲,甚至是更远的物种身上所看到的相同情况,那将是一种极其奇怪的巧合。 “生物平等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它认为人类男性和女性在行为和心理上天生相同。这种观点主张,所有群体在重要的生物学特征上必然是基本一致的,因为一旦承认差异,人们就可能试图从这些不一致性推导出“不平等”,进而导致偏见、厌女症和其他歧视行为。然而,正如我们将要阐明的那样,自然界的客观事实,与我们如何看待不同个体或群体的尊严、权利和自由,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前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后者则是我们如何理性构建道德的伦理问题。